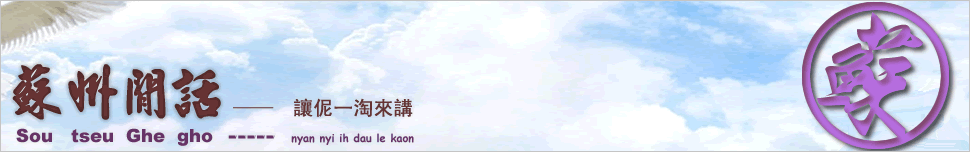苏州人在请教尊姓大名时,遇到黄王不分,或者陈郑不分,常可听到双方都在申明:草头黄、三划王,耳东陈,奠耳郑等等,以免混淆。这不奇怪,吴侬软语与普通话在音、韵、调上的差异之故。让人弄不懂的是,若要问到地名,即使拿出地图来,指正了字眼,也会弄得一头雾水,不知所以。哪怕你同样是吴语系统的上海人、无锡人、杭州人 —— 只有土生土长的苏州人才自己明白。试列几则 :
黄鹂坊,很有诗意,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还写过“黄鹂巷口鹦欲语,乌鹊桥头冰未消”的诗句。到了宋代,不知什么原因改称黄牛坊了。而现在的苏州人却称之为 “ 黄泥坊 ” 。 吴趋坊,是苏州最古老的坊之一。“吴趋”是古代歌曲的名字。晋代陆机曾写过《吴趋行》,诗中写道:“吴趋自有始,请从阊门起”。因此,“吴趋 ” 之称最迟不晚于晋。可是,苏州人却总是叫它 “ 鱼翅坊 ” 。
临顿路,是因吴王率军追击东夷,临时在那里驻扎,停顿休息,所以得名也较早。唐代诗人陆龟蒙曾家住临顿里。想不到苏州人会把“临顿”二字读如英国的首都 “ 伦敦 ” 。
养育巷、由斯弄、钩玉弄( 1972 年改称塔影弄)名字都很雅。苏州人却偏要化雅为俗,分别叫它们为“羊肉巷”、“牛屎弄”、“ 狗肉弄 ” 。
也有化俗为雅的:阊门外鸭蛋桥,其名很俗,一些苏州的骚人墨客就在他们的笔下,写作“阿黛桥”。也许是因为民国时期,这一带正是“红灯区”吧。
宜多宾巷,本作糜都兵巷,是为纪念宋代朝议大夫糜某而命名的。不知什么时候什么原因,改为“宜多宾巷” ,进而更读作“耳朵饼巷” 。耳朵饼是一种不规则半圆形,形如耳朵,甜中带咸的饼。旧时儿童爱吃的零食,现在当然失传了。 乔司空巷,因宋左丞相乔行简所居而得名。苏州人却称之为“乔师姑巷”。师姑在苏州话中是指尼姑,听来总觉得有点奇怪。
泰让桥,是为纪念吴国先祖泰伯奔吴让贤之举而命名,苏州人都叫它“太阳桥”,与原意相差十万八千里。
护龙街是人民路的旧称。在环卫设施普及之前,苏州人家家户户只好用马桶。每天凌晨,居民都把马桶摆在自己家门口,等推粪车的环卫人员来集中处理,因而在街道两旁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马桶,人们形象地将这条贯穿苏城南北的街称为“马桶街”。不过,也有称为“马龙街”的。不管怎样,把“护”字定要转音为“马”字,不知何故。
铁瓶巷,相传唐朝初年有一仙人在此枕铁瓶而卧,醒后遗下一个铁瓶,因此得名。苏州人却称它“铁皮巷”,把好端端的一只瓶,化为一张皮。 都亭桥,相传春秋时期吴王寿梦在阊门内建都亭桥,专门用来招徕四方贤士。据《吴地记》记载,唐时基址尚存。现在苏州人大都叫它“都林桥 ” 。
塔倪巷,据说是孙权建报恩寺塔(即北寺塔)时,造塔所用之泥一直堆到这里,因而得名塔泥巷。如今正式命名为塔倪巷,反而说不出个所以然了。 诸如此类,音转、读别的地名,实在太多,数也数不清。试再举些时常听到的如下:
马医科,叫 “ 蚂蚁(音米)窠 ” ;游马坡巷,称“油抹布巷”;蔡汇河头,索性减为三个字 ——“柴河头”;乘马坡巷,变了“陈麻皮巷” ;马大箓巷,称 “ 马达头巷 ” ;称日晖桥为 “ 石灰桥 ” ;称莲目巷为“莲蓬巷”;称织里桥为“吉利桥”;称西津桥为“西星桥”;有哲学味道的因果巷,转眼成了人人喜爱的“鹦哥巷”;南濠街,叫“南傲街”;梵门桥弄,叫 “ 眼门桥弄 ” ;邵磨针巷,非夷所思,变了 “ 撞木钟巷 ” ;称胥门为 “ 西门 ” ,葑门为“ 付门 ” ;称大小柳枝巷为 “ 柳贞巷 ” ;谢衙前,成了 “ 象牙前 ” ;殿基巷,自然而然成了盘中美餐(现在是保护动物) “ 田鸡(青蛙)巷 ” ;称镇抚司前为 “ 镇福寺前 ” ;称盛家带为 “ 盛家对 ” (不知哪家错);称中由吉巷为“中油鸡巷”(又是美食);称调丰巷为“调粉巷”等等。从字音、字面上看,都与原名相距很远,甚至觉得有点儿滑稽。
另外,苏州人对邻近城镇也有特殊读法。如称吴江芦墟为“芦区”,震泽为“进闸”(不知有否出闸);吴县陆墓为“落呒”;称浒墅关为“许墅关” ,还说成是乾隆老倌第一个读错的,不知是皇帝情结,仰或老百姓的幽默;称唯亭为“移亭”;称阳澄湖为“扬长湖”(不知是否还有避短湖)。
为什么临顿路叫作 “ 伦敦路 ” ?为什么浒墅关称之为“许市关”?为什么葑门变成了“富门”?这些问题似乎一直使苏州人感到大惑不解。我从小听惯的说法是 —— 苏州人好读白字。对这种自嘲,我以前也深以为然,但自卜居香港之后,对这个问题渐渐有了不同看法。这一方面是因为数十年来将粤语、吴语和普通话相互比较印证,颇能使人省悟;另一方面是因为性喜聚书,闲来翻阅旧籍,往往从中发现疑难问题的现成答案。因此,收到家兄寄来的《苏州杂志》 2000 年第 6 期,拜读了《弄不懂的苏州地名》一文后,抽空想提出自己的一点浅见。
苏州一些地名的读法和常音不同,我认为并不都是讹称,其中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吴语的语音起了变化,但某些地名仍读如古音,故而和今音有了差别;二是一些地名更改了,但苏州人的习惯改不了,叫法一仍其旧,于是也造成了字面和读音的不同。
中国的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语音变化不易觉察,其实这种变化是在潜移默化间不断发生的。只要将老一辈苏州人和今日青少年的口音作一比较,便会发现有很大不同。如果说数十年间语音已有明显变异,那么数百年,甚或数千年,其差别之大就可想而知了。不过,古音常常会在口耳相传的用语中留下种种蛛丝马迹。例如,苏州的善男信女念佛,“南无阿弥陀佛 ” 这六个字中,“南”、“无”、“阿”三字的读法和今音便已大相径庭。其实这句佛号的读法,仍接近于古音的缘故。
先说临顿路。苏州人把这个历史悠久的地名叫作“伦敦路” ,正是古今音不同的典型例子。何以见得“伦敦”是古音呢?我想举出三点依据。依据一是古代的字书。按宋代的《集韵》和元代的《古今韵会举要》, “ 临 ” 字的注音都是“犁针切”;明代的《洪武正韵》则是“犁沉切”。所谓切,即反切,是中国古代的注音方法。用现代的概念来解释,就是将上字的声母和下字韵母相拼,再以下字的声调读出。如果我们用苏州话把“犁针”或“犁沉”反切,得出的发音不正是“伦”么?依据二,是口语中和“临”同音的字(即在普通话中都读作lin)。语音变化后,古音往往仍保留在部分口语词汇中,例如苏州人把鱼鳞叫作“鳞爿”,这个“鳞”字,如何发音,想来无须赘述了。依据三,是以粤语作旁证。广东地处岭南,从前山高皇帝远,受近代官话影响较小,保存古音因而也较多。如果谁有相熟的广东朋友们,请他用广府音读“临顿”两字,他会读成“lun dun”,就好像苏州人说“伦敦”。
古音保留在地名中,在全国各地其实都可找出不少例子 。例如,广东省有个县名为番禺,这个“番”字如果照本音读,是要让广东人笑痛肚皮的,他们叫作“潘禺”。为什么“番”会变成“潘”?原来古汉语中本来没有唇齿音,今天声母为f 、 v 的字,古代声母原是 p 或 b 。“番”和“潘”古时同音,后来“番”字读音变化了,但“番禺”这个地名世代口耳相传,依然照老样子叫,于是便成了 “ 潘禺 ” 。
那么,苏州人称葑门为 “ 富门 ” ,是否也因为依照古音呢?这倒不是,“葑”字从来就读若“封”,这里涉及的,是另一种情况,即地名虽已变更,但苏州人的叫法没有跟着改变。 “ 富门 ” 这一叫法,由来已久,宋代名臣范成大主编的《吴郡志》卷三即说葑门:“今俗或讹呼富门”。不过,这句话有两处语病:一是“今”, “富门” 的叫法并非始自宋朝,而应再上溯一千多年;二是“讹”,“葑”变成“富”不是以讹传讹,而是另有道理。这个道理,其实在《吴郡志》卷四十八《考证》中已剖析得很明白。考证者引用唐代张守节所著《史记正义》,指出苏州本无东门,越王伐吴时,梦见伍子胥“令从东南入”,越王于是“筑坛祭子胥,乃开渠,自罗城东开门入吴”,当时“有**随涛入,故以名门”。所谓“**”,即江豚,俗称江.,在今天已是濒危动物,但在二千多年前,原来在苏州偶或也可见到,并为位于苏州东南的这个新开城门带来其名称。苏州人所说的“富门”,其实是“X门”,或“X门”。“XX”两字今天声母虽然不同,但古代没有唇齿音,两字都和“富”音相近。后来“X门”更名为“封门”,取“封禺之山”之意(见《吴郡图经续记》),以后又改为“葑门”,但苏州人仍按春秋时代的老习惯,叫作“X门”。
苏州人把浒墅关称作 “ 许市关 ” ,也和地名更改有关,但又是另一种缘故了。每逢苏州人提到“许、浒”之讹,乾隆皇帝便会在皇陵地下打喷嚏。这自然是一大冤案,因为这一谬误的流传,根源远在一千多年前。当时正是兵荒马乱的五代十国时期,太湖流域是李知诰南唐和吴越国的势力范围。据元代高德基的《平江纪事》,浒墅关本名“虎*,至南唐讳琥(与虎同音),钱氏讳 * (与 * 同音),遂改名为许市。后人讹旧音,于许字加点水为浒,市讹为墅。”千馀年来,“许市”这个名称早被苏州人叫开,但是与此同时,“浒墅”这一写法也固定下来,因此而出现了一个音字不符的千古之谜。
接下来想谈谈养育巷、 因果巷、乘马坡巷等巷名。很多人诟病苏州人把这些十分雅训的地名 “ 讹呼 ” 为羊肉巷、鹦哥巷、陈麻皮巷。这其实又是一宗冤案,因为千百年来,早在这些 “ 雅名 ” 出现之前,苏州人本来就一直是这么叫的。证据何在?可查一查差一点连中三元的明代苏州才子王鏊所编的《姑苏志》。此书中根本不见著录 “ 养育 ” 、 “ 因果 ” 之类巷名,却提到 “ 乘鲤坊巷俗名鹦哥巷 ” ,永安巷 “ 俗名羊肉巷 ” 。而所谓 “ 乘马坡巷 ” ,书中记载正是 “ 陈麻皮巷 ” 。
由此看来,在明代末叶或是清代,苏州曾出现过一场 “ 文革 ” ,横扫过一切被认为粗俗的街巷名称。其办法或是在意识形态上将之拔高,例如 “ 羊肉 ” 易名 “ 养育 ” (使人联想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人皆唱的 “ 爹亲娘亲不如——” 一歌), “ 鹦哥 ” 改为 “ 因果 ” ;或是在字面舞文弄墨加以美化,于是 “ 牛屎弄 ” 变 “ 由斯弄 ”, “ 狗肉弄 ” 成了 “ 钩玉弄 ” , “ 陈麻皮 ” 则摇身一变成为 “ 乘马坡 ” 。可惜市井细民不吃这一套,依然 “ 羊肉 ” 、 “ 狗肉 ” 般叫,真是枉费了红卫兵祖师爷的一片苦心。
苏州城内外并非读别的 “ 讹称 ” 还有很多,但大致不出以上两大范围:震泽呼作 “ 进闸 ” 、陆墓叫 “ 陆 m” 、阳澄湖变成 “ 扬长湖 ” 等,都可归于保留古音一类;西美巷称为 “ 西米巷 ” (按明代《苏州府志》和《姑苏志》,该巷原名 “ 米巷 ” )、梵门桥弄称为 “ 眼门桥弄 ” (唐代陆广微《吴地记》著录为 “ 雁门桥 ” , “ 雁 ” 字古音近 “ 眼 ” 。)、唯亭称为 “ 夷亭 ” (《吴地记》: “ 阖闾十年,东夷侵逼吴地,下营于此,因名之。 ” ),则属沿用古名了。不过,也有个别地名是苏州人故意读别的,乔司空巷即是其例。苏州人都把这条巷叫作 “乔师姑巷 ” ,位列三公的 “ 司空 ” 沦为三姑六婆的 “ 师姑 ” ,堪发一噱,但若照正字面读,司空音近 “ 屎孔 ” ,恐怕许多淑女绅士都会感到难以启齿吧。
那么,是否所有的 “ 讹称 ” 都错得有道理呢?当然不是,确是读别的地名不但自古就有,而且很多,例如谢衙前成了 “ 象牙前 ” ,都亭桥成 “ 都林桥 ” ,泰让桥成 “ 太阳桥 ” 等,都是很典型的例子。又如糜都兵巷先讹为“ 耳朵饼巷 ” ,后在 “ 横扫一切 ” 中雅化为 “ 宜多宾巷 ” ,游墨圃巷被谑称为 “ 油抹布巷 ” 后,易名为“ 游马坡巷 ” (想来跟 “ 陈麻皮巷 ” 改为 “ 乘马坡巷 ” 同出一手,不知此公为何特别锺情于 “ 马坡 ” 二字。)更使 “ 讹称 ” 的问题变得错综复杂。
不过。贯穿苏州城的人民路旧时为什么叫作 “ 马龙街 ” ,促狭一点的甚至叫作 “ 马桶街 ” ,却真令人难明究竟了。人民路旧称 “ 护龙街 ” ,清帝南巡前则为 “ 卧龙街 ” 。 “ 护 ” 与 “ 卧 ” 字均与 “ 马 ” 相去甚远,按理不可能音转。但若依上述 “X 门 ” 、 “ 夷亭 ” 、 “ 雁门桥 ” 等地名更改一二千年后苏州人仍坚持用旧名的例子,那么或者可以大胆假设,人民路在唐宋或更久远的时代,曾名为 “ 马龙街 ” 或与此音近的地名。按 “ 马龙” 即 “ 龙马 ” ,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称 “ 马龙出而大易兴 ” ,若作地名倒是很旺风水的。只可惜《平江图》、《吴郡志》等较早的文献资料对坊桥寺观的记载巨细无遗,却偏对这么一条南北通衢不著一字,令人难找依据,只得信口开河了。 还保存着两支老秤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