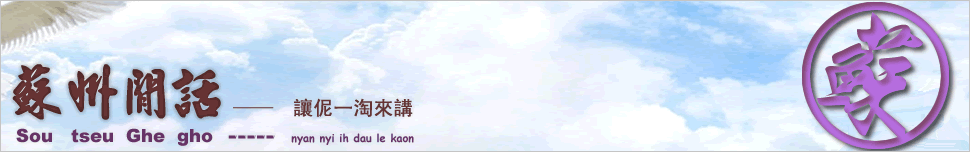古今语言都有方言的地域差异,人们也很早就认识到方言的存在,《礼记·王制》就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王充《论衡·自纪篇》更认为“经传之文,圣贤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正确地说出了经书难懂的原因,一是古今语言有历时的变化,二是又有共时的方言差异。
汉语包括七大方言,即官话、吴语、赣语、客家话、湘语、闽语、粤语。吴语大致分布于江苏长江以南的常州、无锡、苏州,包括镇江的丹阳、南京的高淳,长江以北的南通、海门、启东、如东、靖江,上海全境,浙江除淳安、建德、苍南、平阳之外的地区,以及江西的上饶,福建的浦城北部。安徽的铜陵、太平说宣州吴语,但宣州吴语受到江淮官话的严重渗透。吴语使用人数约占汉族总人口的百分之八,仅次于官话使用人数,属于汉语第二大方言。
方言是语言逐渐分化的结果,而语言分化是从移民开始的,人口迁徙在促进文化发展的同时,也使语言发生很大变化。在七大方言中,官话可以看作是古汉语数千年来在北方发展的结果,其余六大方言则是由于北方不断向南方移民逐步形成的。秦汉以前,江南土著使用古越语,与古汉语相差很远,不能对话。秦汉以后,北方汉人先后几次大规模南迁,带来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北方古汉语,分散到南方各地,逐渐形成互相歧异的六大方言,吴语在六大方言中是最早形成的。
周秦时期,今江、浙、闽、粤一带为百越族所居,《汉书·地理志》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百越人即今壮侗语族居民的祖先。刘向《说苑·善说》记载了一首春秋时的《越人歌》,故事中人鄂君子晳说:“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可见越歌听不懂,得借助楚语翻译,刘向用汉字记音,并以汉文作了翻译。据考证,这首《越人歌》使用的语言与壮语关系密切,可见古越语很可能是壮侗语族的母语。古代吴越是异国而同族,诚如《吴越春秋》所谓“同音同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两国的语言应该是相通的。这从先秦两汉的历史地名中可以得证,如於越、於陵、於菟、句容、句余、句注山、姑苏、姑蔑、夫椒、乌程、乌伤、余杭、余暨、余姚、无锡等,它们一是冠首字类同,个别字写法虽不同,但求之古音,则相合或相近;二是都属齐头式,古越语的特征十分明显。
史籍上关于泰伯奔吴的记载,暗示着北方移民的一次南徙。北方移民原有的方言是否能在当地流行,与百越族相处数百年后能否在日常说话中保持下来,都大可怀疑,因为他们连人名都古越语化了,如句吴、句践、句亶、余善、余祭、余昧、夫差、夫概、无余、无壬、无颛、无疆等,与吴越地名的语言特征相同。然而吴王、越王们所铸的礼器、兵器上都镌刻汉字,季札更谙熟中原礼乐,因此可以认为,吴越的贵族阶层学习并使用北方汉语。
一般认为,原始吴语源于古楚语。上古时期,南方汉语只有楚语,楚语正式进入吴越地区,当由楚灭越开始。《汉书·地理志》称“本吴粤(越)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经楚人几十年的统治,形成当地发展汉语的条件,楚语在吴语尤其南部吴语的形成中应起过重要作用。今老湘语与吴语有许多共同之处,似非偶然。原始吴语的形成,以古越语为底层语言,汉语上接受了楚语的影响,故历来有吴人“音楚”之说,《乐府诗集·郊庙歌辞》就说:“梁陈尽吴楚之音,周齐杂胡戎之伎。”这一方言发展痕迹,同样也“倒流”于今江西波阳一带,《大清一统志》就记饶州府“语有吴楚之音”。
秦汉置郡设官驻兵,中原移民主要聚居于郡治吴(今苏州)、会稽(今绍兴)、宛陵(今宣城)及秣陵(今南京)等重镇,吴语就以这些地方为中心发展起来,故后来吴语还是以苏州为苏南吴语中心,绍兴为浙江吴语中心,宣城为皖南吴语中心。但当时越族力量还很强,部分越人进入山区成为“山越”,而浙南、福建一直还是越人的天下。直至三国时,许靖致曹操书中还说自己从会稽“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故扬雄《方言》记吴越方言词主要还是侗台语词汇。
至西晋永嘉丧乱之前,建康(今南京)一带还是纯粹的吴语区,南朝乐府中的吴声歌曲,就是用吴语传唱的歌谣,其中保存着一个典型的吴语词汇“侬”。《晋书·乐志》称“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吴声歌曲不但在建康一带广为流传,并且久已形成,西晋初就传入北方,《世说新语·排调》记了这样的故事:“晋武帝问孙皓:‘闻南人好作《尔汝歌》,颇能为不?’皓正饮酒,因举觞劝帝而言曰:‘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桮酒,令汝寿万春。’帝悔之。”这《尔汝歌》也就是吴声歌曲。永嘉丧乱后,来自苏北、山东的大批移民徙入,先后在那里设置侨郡、侨州二十余处,移民人数约百万以上,超过了土著,并且移民中不少是大族。《颜氏家训·音辞》写道:“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当时中原旧族多侨居江左,故南朝士大夫所言,仍以官话为主,而庶族所言,则多为吴语,故“南方士庶,数言可辨”;而北方士庶,语音无异,故“终日难分”。惟北人多杂少数民族语音,反不若南朝士大夫之彬雅。至于闾巷之人,则南方之鄙俗,不若官话切正。由此可见当时建康一带方言交融的现象。北方士族对吴语有两种态度,《世说新语·轻诋》记道:“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颈乌,但闻唤哑哑声。’”王氏兄弟是学说吴语,支遁则讥笑为鸟语,态度是迥然不同的。然而连王导也在学说吴语,可见这是当时的一种风尚,《世说新语·排调》记道:“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吴人以冷为渹)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惟闻作吴语耳。’”南方士族则都学说北来雅音官话,但其中也有不少人并不放弃自己的方言,《宋书·顾琛传》便记道:“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变。”《南齐书·王敬则传》也记道:“敬则名位虽达,不以富贵自遇,危拱彷遑,略不衿据,接士庶皆吴语,而殷勤周悉。”这就形成南北互学方言和双语并行的现象。但终因为北方移民在人口、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优势,不但使今南京、扬州等沿江吴语官话化,并且影响周边地区,使之发展为带有一定官话味的吴语,即以太湖为中心的北部吴语,以青弋江为中心的西部吴语(宣州吴语),而距离南京较远因而发展较慢的南部吴语,则较多保留原始吴语的特征。
至唐代,由于国家安定兴盛,吴语相对稳定,得以巩固和分化。至北宋,吴语不但已经巩固,并形成今天南北各片的基本状况。靖康之乱,宋室南渡,大量北方移民至杭州,移民数倍于土著,使杭州语言发生变化,带上了官话的特点。因北方移民基本集中在临安府城内,故时至于今,杭州“半官话”的分布,也就在杭州市区的范围。
移民活动又给吴语区带来双语现象,这是由于移民的人数较少,经济、文化上的地位相对较低,不得不学会吴语以求生存,但他们往往是大分散小聚居,有意识地保留原有的风俗传统,故在自己家庭和移民社区仍然使用原有的方言。今苏州太湖之滨,有许多祖籍河南、湖北的居民,约在太平天国战争后迁入,被称为“客民”或“客边人”,如吴江菀坪就是这样。
就大势而言,今吴语区的历史是由北向南开发的,春秋战国时汉人活动中心在今苏州、绍兴、诸暨一带。秦汉时期,浙北、苏南依次开发;三国两晋以后,始将开发范围推向浙南;唐以后扩展到浙西及边境地区,吴语也相应由北向南扩散。春秋时期南进的移民大约是从今宁绍、杭嘉湖平原出发的,他们越走越远,方言也就与古越语越来越歧异,以致后来浙南移民的方言与出发地的方言竟不能通话。从现代吴语考察,从北到南在地理上有一个渐变的过程,这在词汇、语法、语音上都有所反映。
移民活动是方言形成的主要因素,但还有其他的因素,如行政区划中心变易也使方言变化。行政区划中心一般是这一政区内政治、经济、文化、时尚的中心,也一般是当地最大的城市,对人的语言心理有向心力,一旦中心城市变换,当地的权威方言也势必随之变换。如华亭县宋代就属嘉兴,元至元十五年(1278)改松江府,仍属嘉兴道,而上海系由华亭县析置,故上海话源于华亭土话,嘉靖《上海县志》就称“方言以华亭为重”,而华亭土话则与嘉兴话接近,正德《松江府志》和正德《华亭县志》在述及方言时都说:“府城视上海为轻,视嘉兴为重。”至清代,松江府隶属江苏省,嘉兴话的权威才让位给苏州话,康熙《松江府志》就说:“府城视上海为轻,视姑苏为重。”嘉庆《松江府志》也说:“府城视上海为轻,视苏州为重。”
吴语虽然历史悠久,但在表现形态上却不算最古老,因为三千年来,它不断受到北方官话的强烈影响,比较原始的吴语反而保留在闽语里。当然在吴语中仍然保存着一些在多数现代汉语方言中已经消失的古汉语特点,其中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保持了浊音和清音声母的分别,现在吴语中的“浊音”包括“清音浊流”(分布在北部吴语区)和“真浊音”(分布在浙南)。
**请各位朋友尊重的作者的版权,如果我们不慎侵犯了您的版权,请您及时联系我们,我们也会立即做出回应。